黄敏散文《昔我往矣 垂柳依依》-凯发k8网址首页
2020年03月18日 11:56 有人参与 条评论小时候,在村东头折几根柳枝回来,随意插在池塘边自家宅基地里,多年以后,柳枝条已长成池边大柳。
两棵柳树树干粗大,枝条柔曼,叶色青翠,犹如两把绿绒大伞,擎在池边一隅,抵挡酷暑严寒,荫蔽方寸土地。
每每亲近,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轻抚那一层层嫩绿,亦让嫩绿搓揉我的脸庞。拥抱这层绿,心中不免升起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无限感慨!垂柳依依,已不忍离。

柳树边便是晒谷场。
农闲日,阿哥们在谷场简易的篮球架下挥汗搏杀,我们几个小不点在篮筐底下专干捡漏的活计。偶尔抢到球漏,并没有立马将球扔给人家,而是快速溜到边角处,来个“擦板”颠入,快意非常。可误了人家的赛事,不免招来几顿训斥,训斥声中,也还掺杂着几许夸奖:有姿势有实际!从此,我便爱打球了,而且这种喜爱一直贯穿始终。
入夜,阿姐们在谷场上柳树边彩排样板戏《红灯记》。陈家三姐扮演李铁梅。三姐的扮相可好看了。三姐那年读初二了吧,人长得水灵水灵的,头扎两条长辫子,化妆时两条长辫合为一条,辫尾儿上系根红绳,插躲小红花,红格子衫穿上,俊俏得很咧。只见三姐唱道:“听罢奶奶说红灯,言语不多道理深,为什么爹爹、表叔不怕担风险,为的是:救中国,救穷人,打败鬼子兵。”看了三姐的彩排与演出,觉得三姐就是李铁梅,李铁梅就是三姐!第二天,三姐的唱词我们大都忘记了,我和阿弟上学时嘴上只懂哼一句:我家的表叔,数---不---清!
除了看戏,电影还是会不时看到。什么《地雷战》,《地道战》,《小兵张嘎》,看得过瘾,看了十遍还是想看。没位置的时候就爬上柳树斜着看,外村穿田过村来观影的,实在挤不下,就在银幕的反面凑个热闹。我们在正面看到小嘎子右手拿枪,他们看到的是相反的影像,这边枪响,那边胆子小的就吓得溜号,也有不小心摔进池塘的,“扑通,扑通”几下,引来一阵阵欢笑声……
没戏看没电影欣赏的夜晚,我们就聚集在柳树旁,听老奶奶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。牛郎和织女都讲过那些话了?我们都忘得一干二净咯,记忆中只留存,那头牛是头忠厚老实的牛!听完故事,我们几个小伙伴便相邀在稻草堆里玩捉迷藏。我爬到柳树上躲起来,小伙伴们愣是找我不着,我甚为得意。邻屋阿三长得胖,是站着都能睡得着的主儿。大半夜大人们找来时,掀开草垛,发现他在草堆里头睡得正香呢。
哦,池边垂柳依依,带不走的故园情!
阔别故乡经年,我于去年春节前重返故里,想寻觅久远的依依垂柳情。
听弟弟说,那两棵柳树已经被砍掉了,原谷场重新翻修,新建了灯光球场,池塘边上也修建了村文化中心。听闻柳树被砍去,我心中难免有点难过,但转而又想,为了扩建文化中心,几个生产小组及村民无偿捐出了土地及房房,这两棵柳树砍了就砍了吧,为新农村建设让道,也是柳树物有所值,不必介怀。我也为文化中心捐了款,这回得去看看新生事物了。
溜达到柳池边,不知谁人在原柳树地种上了十几棵不伦不类,大煞风景的“速生桉”!速生桉树旁,几座平房紧挨球场而建。一座平房的屋檐下,两张四方桌摆放其中,十几个老妪少妇,外加几个光着膀子,手臂上纹着青龙白虎的青年围坐一团,气壮如虹。只见纹身男手握骰子,口中念念有词:“买定离手,买定离手!”然后大呼一声“走起”,手起色落。“庄家九点,通杀!”十元、二十元、五十元乃至一百元面值的纸币瞬间归入庄家囊中。“唉,我的八点,还是干不过庄家!”少妇面带愁容。“再来再来,我就不信你盘盘手气这么好!”我仔细一瞧,是屋上四婶。老婶子七十有几了吧,这赌性不输后生啊!
屋外赌兴正浓,屋内则将声四起!进得屋来,一眼扫去,房间不大,却摆了四张麻将桌,除了12名麻友,桌子边上还围着不少看客。“我*!三六九不叫,偏要叫二五八!衰衰衰!”一声哀叹,在烟雾缭绕的窄小空间里弥漫开来,整个屋子里充满了阴气和晦气!
“弟弟,文化中心就没别的活动了?”从乌烟瘴气的环境中出来,我问问随行的弟弟。
“中心刚落成时蛮热闹的,打球的,跳广场舞的,气氛挺好,但不知什么缘故,自从赌风盛行,就不见几个人跳舞,球场也没见开过灯了。”弟弟也很无奈。
“前几天,东头大头六打麻将输掉了三万块,在海南岛辛辛苦苦做装修工赚回来的血汗钱,一夜之间全输掉了,两公婆正在闹离婚呢。”弟弟补充道。
日近黄昏,我和弟弟在村里新修的水泥路上踱步前行,偶尔回头望望文化中心,灯光闪烁处,是我儿时栽种柳树的池塘,池塘边上有几座矮房子,矮房子屋里屋外正热闹非常,可这热闹,不是我儿时所见到的热闹。
我儿时的热闹还会回来么?
想起我的依依垂柳,我蹲坐路边,抱头痛哭起来……

1、凡注明来源为“东莞阳光网”的所有文字、图片、音视频、美术设计和程序等作品,凯发k8网址首页的版权均属东莞阳光网或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所有。未经本网书面授权,不得进行一切形式的下载、转载或建立镜像。否则以侵权论,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2、在摘编网上作品时,由于网络的特殊性无法及时确认其作者并与作者取得联系。请本网站所用作品的著作权人直接与本网站联系,商洽处理。
联系邮箱:tougao0769@qq.com
相关阅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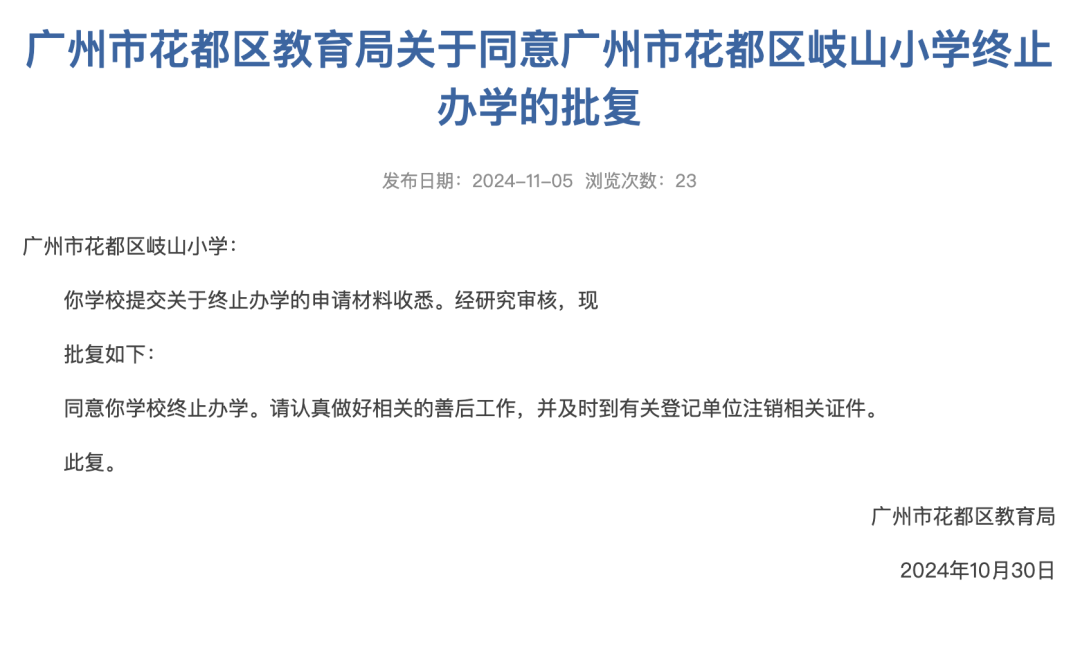


网友跟贴